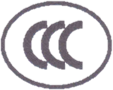這(zhè)次去浙江安吉(jí)鳳凰高(gāo)爾夫球場打球,沿途成片成片的竹林,無邊(biān)翠綠,隨風起舞,宛如海洋。我的(de)思緒(xù),隨著延綿的竹浪,回到了故鄉,回到了孩時,勾起了那靈魂深處的竹之情結。
我生長在湖南寧鄉的稽嘉山(shān)下,現在還清晰記得,山穀山坡,水邊地旁,庭前屋後,到處是成片的楠竹,而數(shù)量集中品質最好的竹林,當屬塔子山溝(gōu)。說是山(shān)溝,其實是一片並不開闊(kuò)的(de)山(shān)穀。那片竹林,沿山(shān)澗溯流而(ér)上,從山穀逆(nì)坡而爬,密密麻麻,大小相間,一株比一株高,根連著(zhe)根,葉挨(āi)著葉,延綿不絕,蔚成竹海。
窮(qióng)人(rén)的孩子早當家,十來歲開始,就得上山砍柴(chái)火。去竹林裏砍灌木,是夥伴們喜(xǐ)歡的選擇。濃密的竹枝遮擋了烈日,渴了喝口清冽的山泉,稀疏的柴枝容易下刀,係柴(chái)火時順手(shǒu)披兩根(gēn)低矮的竹枝就地解決,偶(ǒu)爾還能拾到可口美(měi)味的竹苼……年幼的我們(men),在勞動中學會了(le)去繁就簡,學(xué)會了過程中享受快樂。
竹的用途,被開發(fā)到淋漓盡致。新陳代謝後枯黃的竹葉灑落地麵(miàn),三五(wǔ)天就有一層,收集起來,一筐一(yī)筐的(de)擔回家,是不錯的燃料;春天破土的春筍,冬天地(dì)下的冬筍,是餐桌上的(de)佳肴,多餘(yú)的曬成筍幹,是青黃不接時節下飯的美味;剝落(luò)的(de)筍殼,是紙漿的(de)上好原料;竹子生長四五年(nián)後,陸續砍倒,大一些的用來蓋房,小一點的(de)請(qǐng)篾匠(jiàng)製成籮筐、竹席、竹椅、簸箕等各種各樣(yàng)名(míng)目繁多的工具、家具和用具(jù);竹枝摘葉後紮成掃帚,竹尾削(xuē)光後做掃帚把……竹製品和掃帚(zhǒu)自家用不了那麽多(duō),成批的販出,是一筆很大的收入——孩子們的學費也在其中。
從祖輩開始,人和竹一直和諧相處。密集的春筍,才能間隔挖幾個上餐桌(zhuō);不到四年的成年竹(zhú),不能(néng)砍倒;竹枝(zhī)不能隨意披掉;竹身不許刻劃;地下的竹鞭,絕不許挖斷。是啊,和諧相處,不濫砍濫伐,這母親般的竹林,得以生生不息(xī),世代常青。
竹林有三災,春天的颶風,夏天的蝗災,冬(dōng)天的冰災。雨後春筍節節高,長得兩三丈高時,下身已成(chéng)竹,上身還是筍,一場颶風,筍尖盡數折(shé)斷,留下竹身仰(yǎng)天長歎;夏天竹葉繁茂,香甜可口,蝗(huáng)蟲大軍掠(luě)過,寸葉不留;嚴冬遇上湘楚大地(dì)的(de)潮濕(shī)空氣,冰(bīng)淩愈來愈厚愈來愈重,爆竹聲此起彼伏,成片的竹林爆裂倒(dǎo)下。一場災難過(guò)後,要很多年才恢複元氣。
我在(zài)十二三歲時,學會了做篾活,劈竹,破篾,織涼席,編鬥(dòu)笠,像模像樣。還(hái)創造性的織(zhī)了兩個竹燈(dēng)罩,糊上白紙,十瓦的白幟燈亮度能超過五(wǔ)十(shí)瓦的。那個手(shǒu)巧啊,大人誇讚,夥伴羨慕。村裏一(yī)個有名的篾匠給我媽說,長大了把(bǎ)他女兒嫁給我。遠在家鄉(xiāng)的姑娘,你現在可(kě)好?
寫到這,忽然有個假設:當年,不拚命讀書走出來,留在那大山腳下好好(hǎo)做個篾匠,那我的人生,又是怎樣一番天地呢?